东亚为什么盛产「做题家」|大象公会
2020/7/30 22:04:08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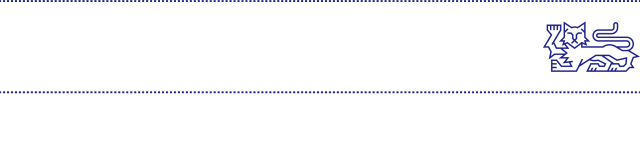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
文|张蔓生
做题家是中国小镇的特产吗?
当然不是。放眼世界,整个东亚都是做题家的高产区。
「东亚做题家」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还被编成表情包,活生生将「Asian nerd」(亚洲书呆子)和「exam hell」(来自日语「受験地獄」,形容考试竞争激烈)变成了国际流行词。

· 英文社交媒体 Reddit 上流传的「亚洲学霸的高中标配」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论是「美国高考」SAT,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 PISA(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 TIMSS、单测读写能力的 PIRLS*,甚至单门学科竞赛 —— 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
这种优势在小学学段就表现出来,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在只测数理学科的 TIMSS,中国大陆没参加,东亚各组还是甩下别人一大截。

· 2015 年的 TIMSS 数学测试。在四年级组,东亚最后一名的日本,比其他国家的第一名还整整高了 23 分。到八年级组,差距更是拉大到 48 分。TIMSS 是美国学者设计的 / 图片来源:[1]

· PISA2015 国际成绩地图。这张图显示的是各国家和地区所有三科的平均成绩,分数为绿>黄>红。几乎在所有国家,PISA 的采样点都是在发达城市,但这届中国大陆仍被广东拖了后腿,跌倒第十,在下一届换成浙江才又成功登顶
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均教育投入,乃至智商,都无法完全解释。

· 《经济学人》统计了近年来各国 PISA 成绩的变化,并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6-15 岁人均总投入 5 万美元)时,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
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边际效应。当投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再往里投更多的钱就没什么用了。这时,更复杂的因素开始起效。
东亚人民对做题和考试的狂热,究竟来自哪里?
东亚人为什么爱做题
长久以来,中文舆论都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归因于某种「科举情结」。

· 本文发表于 2006 年,作者张奠宙先生(1933-2018)是享誉国际的数学教育家
不过,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东亚做题家」的影响因素之一。
首先,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他们只在最高层官僚中占据优势,而在整个帝国,不经考试、通过恩荫、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
其次,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韩国、越南同中国一样,长期开展科举,新加坡则没有科举,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在港、澳、台等地,科举文化的存在感也不强。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港、澳、台并不相同,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差异更大。有的是「一考定终身」,有的是多次考试,有的是连考带申;有的是统一录取,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
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做题家」的行列。
这些教育体系有如下共同特点: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做题练习、普遍的补课班,以及看重考试,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若以 PISA 和 TIMSS 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东亚第一「做题家工厂」还并非中国大陆,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同样遍地是补习班。一个新加坡学生不但要勤刷题、会考试,还要培养各种特长,才能被称为优秀。

· 《经济学人》曾撰文称,新加坡教育有三样值得学习的法宝: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以及更出色的教师。有中文媒体将其简化为「习题册,强制补习,善待教师」
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更加内卷化、筛选性更强。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

· 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升学流程
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从三年级的优才班(GEP)选拔,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PSLE)。

· 虽然中国取消了大部分小升初考试,但学生们实质上仍要面对这一轮筛选。图为合肥某中学的小升初考试
和中国相似,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67% 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 850 所补习班上课,每年花费 11 亿新加坡元。

· 不过,在月收入低于 4000 新元的家庭,只有 20% 的孩子上补习班 / 图片来源:[2]
由此,「考试指挥棒」决定了国家的整个教育生态。
这套听上去十分熟悉的筛选性教学理念,源头叫做 meritocracy,一般翻译成「精英治国」。它指的是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目的是筛选出精英,让他们掌握权力。
「精英治国」这个词在西方左翼的自由主义者眼中带有严重贬义,因为「精英」的传递性意味着阶级固化、闭门机制,以及寒门难出贵子。支持这套做法的,大多是右翼。
在东亚,「精英治国」不常被讨论,却大量被实践。
从新加坡到香港、台湾(民主化之前这一特质更为明显),再到日本、韩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殊异,但全都信仰「精英治国」。这很可能是源于近现代东亚地区都曾经历的威权统治史。
这方面,日本堪称先驱。明治维新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也树立了比西方还要严格的精英教育等级观。
威权属性最强的旧日军,堪称「做题家」的海洋 —— 军校全都靠考,难度颇大;毕业院校和在校成绩,基本决定了军人的晋升速度和生涯高度。这种对在校成绩的极端重视,在全世界军队都是绝无仅有的。

· 旧日本陆军等级森严,仅围绕陆军大学校即有以下阶级:军刀组(陆军大学优秀毕业生)优于天保钱组(普通陆大毕业生),天保钱组优于无天组(考陆大失败者),其下陆军士官学校还能再分。海军则直接按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考评成绩排列吊床号,吊床号就是每个人晋升和任命的职位顺序,且规定靠后者不得指挥靠前者,绝无晚辈逆袭的可能
比起说一不二的专制政府,威权统治是尴尬的。虽然小圈子垄断权力,但还得表现出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无论是赤裸裸的阶层代际传递,还是大众眼中可以被操纵的选拔方式,都会损害其合法性,引发不稳定。
他们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所以,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像古代科举一样,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
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还有以考试为主要进路的科层官僚制。发达的科层官僚制也正是东亚政治的最大共性。
东亚之外的「做题家」
世界上也有些国家和地区,那里的孩子不怎么应试做题,却能在 PISA 和 TIMSS 等国际测评中取得高分。
比如芬兰。该国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讨论课、不做题、少考试、效果好著称,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国集体学习的对象。
不过,和所有的「素质教育」一样,芬式教学有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为一个平等而富裕的社会设计的。如果社会天然存在不平等,那么当基础教育变得高度宽松,家庭教育和课外培训就会拉大这个差距。

· 每年一万多名新移民进入芬兰,并且大多不会说本地语言,对于这个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国家造成冲击,也拉低了芬兰学生们的平均成绩 / 图源:Reuters/Panu Pohjola/Lehtikuva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
有的认为,尽量不丢下一个孩子,让所有国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相对均质的教育资源,这是「平等」。有的则认为,参加同样的考试,成绩好的(不管原因是天生聪颖还是家长肯投入资源)就应该被筛选出来作为精英,这才是「平等」。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加拿大、瑞典,后者的典型则是苏东国家和东亚国家,更多的国家是在两者之间找平衡。这两种教育模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学生,但只有后者会成为「做题家」的海洋。
东亚之外,全球公认的另一个「做题家」产地是前苏东国家。
总体上说,苏东国家的小孩确实更能学习、更会考试。它们教学制度各异,但基本上全是考试导向的,高校大多像中国一样,实施统一招录。(只有波罗的海三国例外)
这些国家也有和东亚同样的现象,比如流行上补习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篇报告写到:
后苏联时期的特征是「课外补习的影子教育系统」的扩大。一方面,补习为学生提供了适当的个人学术发展和成功备考的机会。另一方面,影子教育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并促进新的腐败形式。

· 特别依赖补习班的教育系统,在国际上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图为美国儿童在一家俄罗斯人开设的补习班学习「俄式数学」 / 图源:Jesse Costa/WBUR
在经济水平更低、公共教育经费更少的情况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生们长期在 TIMSS 排前列,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 PISA 名列前茅,表现甚至好过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国家。
这并不是由于其他经济、文化上的原因 ——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
柏林墙倒了三十年了,前东德和西德属地的「做题家」水平至今仍有差距。东德孩子家乡的经济更不发达,教育经费和好学校相对较少,但就是比西德孩子更能做题。

· 德国「高考」Abitur,分数为 1.0-4.0,数字越小成绩越好。图为 2015 年德国各地的平均成绩分布,颜色越浅成绩越好,可以看到前东德属地的成绩整体明显好于前西德
这或许是苏联体制的历史余韵。
勃列日涅夫以来的苏联是高度崇尚精英治国的。勃列日涅夫曾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在苏联制度下,各级学校层层筛选出的优等生可享受种种特权优待,是进入官僚晋升快车道或打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

不过如今,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恰恰来自苏联模式的反动者——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可谓异军突起。从苏联独立之后,它的 PISA 成绩一路从名不见经传到问鼎欧洲,只花了不到三十年。
为了清算苏式教育,九十年代,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复制了芬兰的教育模式,搞起自由宽松的素质教育。自从 2006 年第一次参加 PISA、超过俄罗斯之后,这就成了他们教育成就感的来源。

· 爱沙尼亚(深蓝)和芬兰(浅蓝)的历届 PISA 各项成绩对比图。2006 年的爱沙尼亚尚没有太大优势,到 2012 年已经与芬兰接近。现在,它更是超过芬兰成为欧洲第一
虽然直到今天,更重视做题的俄罗斯学生仍然在「比做题」的 TIMSS 上名列前茅,但爱沙尼亚在唯一参与的一次 TIMSS 上就取得了远超俄国的成绩。
在主要测试思维和逻辑的 PISA 上,俄国不但被波罗的海三国的俄裔学生比了下去,在全球也排不到前面。
「做题家」的套路有效,但并不是万能的。
有办法不再生产「做题家」吗?
学习刻苦、学习效率以及成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国家和地区之间横向比较也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学生要花很长的学习时间来完成课业,成绩却没什么改善。

· PISA 提供的学习时间和「科学」(理化生)成绩的关系。蓝色和黄色分别代表在校和课外学习时间,红点代表学习效率——每多学习一个小时,考试能多得几分。整张图越往右,学习效率就越低。图表最左侧为芬兰
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入选国家里排名很靠后。孩子们花了极长的时间在做题上 —— 每周比芬兰和日本多近 20 小时,甚至比新加坡还多五小时,花了更多时间学习,成绩的增长却不成正比。
大凡培养做题家的教育体系,改变的力量总会指向「减负」—— 虽然在今天,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被等同于学校甩锅、逼家长花钱上补习班,被彻底污名化了。
然而,当教育已经成为军备竞赛,极大浪费社会资源,影响家庭生活质量,降低生育率,并造成阶层的再循环,让所有人同时降低教育投入,可能是终结这种无限内卷的唯一办法。
2019 年,一直不减负的新加坡也开始了「减负」,希望通过取消部分考试、高校扩招和生育率的自然下降,降低教育的竞争烈度。
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极端低下,人口维系主要靠移民,数十年来愿意将「精英治国」贯彻到底。如今竟然连新加坡也开始「减负」,可见这场昂贵的教育军备竞赛对社会的拖累有多严重。

但问题在于,在本就信仰「精英治国」的地方,社会的筛选性并不会随着教育压力的降低而下降。「减负」也只能覆盖公办教育,只要通过考试筛选成为人上人的动力依然强大,减负就很难成功。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等地都曾搞过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但无一达到预定目标。
苏联和俄罗斯也都搞过「减负」,「减负」这个词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俄罗斯时代,却在拉大社会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并未起到「减负」效果。
我们也曾写过日本从 80 年代起推行「宽松教育」,结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同时带来严重的学力下降,又往回开倒车的故事。(详见:被嫌弃的「宽松教育」,终将来临|大象公会)
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都像中国大陆这样,有着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它们宁可在减负和加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的培养「平成废宅」和「做题家」,也不愿考虑让全社会的选拔机制变得更平等、更高效,是否有其他可能。

观念的问题,才是决定性的。
注释:
[1]http://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timss-2015/mathematics/student-achievement/
[2]Private Tuition in Singapore: A Whitepaper Release
http://www.blackbox.com.sg/wp/wp-content/uploads/2012/09/Blackbox-You-Know-Anot-Whitepaper-Private-Tuition.pdf
[3]https://i.imgur.com/jfSecur.png
*注:参与这些测试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完全重叠,也不覆盖全球所有国家。
参考文献:
[1]Leung, Frederick Koon-Shing, Klaus-D. Graf, and Francis J. Lopez-Real, eds.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 and the West: The 13th ICMI study. Vol. 9.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6.
[2]张艳杰. 世纪之交:俄罗斯教育改革研究[J]. 教育探索, 2004(06):52-52.
[3]Khavenson, Tatiana, and Martin Carnoy. "The unintended and intended academic consequence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the cases of Post-Soviet Estonia, Latvia and Russia."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2.2 (2016): 178-199.
[4]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Mathématique. "Discussion Document: The Thirteenth ICMI Study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 and the West."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2000): 95-116.
[5]Tveit, Sverre, and Christian Lundahl. "New modes of policy legitimation in education:(Mis) using comparative data to effectuate assessment reform."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7.5 (2018): 631-655.
[6]Legitim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a and Kenya
[7]Komatsu, Hikaru, and Jeremy Rappleye. "Is exam hell the cause of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case for transcending stereotypes."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4.5 (2018): 802-826.
[8]West, Richard, and Johanna Crighton. "Examination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sues and trends."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6.2 (1999): 271-289.
[9]Kozar, Olga. "The face of private tutoring in Russia: Evidence from online marketing by private tutors."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8.1 (2013): 74-86.
[10]Heyneman, Stephen P. "Uses of examin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lec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ecto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7.4 (1987): 251-263.
[11]Kaiser, Gabriele, Keiko Hino, and Christine Knipping. "Proposal for a framework to analyse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 and the West. Springer, Boston, MA, 2006. 319-351.
[12]Jerrim, John. "Why do East Asian children perform so well in PISA? An investigation of Western-born children of East Asian descent."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1.3 (2015): 310-333.
[13]Leung, Frederick KS. "In the books there are golden houses: Mathematics assessment in East Asia." ZDM 40.6 (2008): 983.
[14]Ono, Hiroshi. "Does examination hell pay off?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ronin” and college education in Japa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6.3 (2007): 271-284.
[15]Ninalowo, Bayo. "Education, legitimation, and crisis."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Revue canadienne de l'éducation (1984): 298-316.
[16]Carnoy, Martin, Tatiana Khavenson, and Alina Ivanova. "Using TIMSS and PISA results to inform educational policy: a stud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urs."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5.2 (2015): 248-271.
[17]Mikk, Jaan. "Students' Homework and TIMSS 2003 Mathematics Results." Online Submission (2006).
[18]Waldow, Florian. "What PISA did and did not do: Germany after the ‘PISA-shock’."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8.3 (2009): 476-483.
[19]Blossfeld, Pia N., Gwendolin J. Blossfeld,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Long-term changes for East and West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2 (2015): 144-160.
[20]Khavenson, Tatiana, and Martin Carnoy. "The unintended and intended academic consequence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the cases of Post-Soviet Estonia, Latvia and Russia."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2.2 (2016): 178-199.
[21]康晓茜, 魏李飞. 苏霍姆林斯基的"减负"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基础教育研究, 2017(15):40-42.
[22]张广英. 苏霍姆林斯基减负理论的启示[J]. 山东教育, 2001(11):5-6.
[23]钱同舟. 苏霍姆林斯基的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思想及其启示[J]. 教育与职业, 2005, 000(016):44-45.
[24]Why Thousands Of American Parents Are Sending Their Kids To 'Russian Math'
https://www.wbur.org/edify/2017/04/13/russian-math-school
[25]新加坡补习中心现象再思考,联合早报,2017年1月2日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70102-708821
[26]Tuition in Singapore – Statistics, Facts and Advice (2020)
https://smiletutor.sg/an-overview-of-tuition-in-singapore/
[27]7 in 10 parents send their children for tuition: ST poll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7-in-10-parents-send-their-children-for-tuition-st-poll
[28]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the latest PISA test results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16/12/10/what-the-world-can-learn-from-the-latest-pisa-test-results
[29]Pisa rankings: Why Estonian pupils shine in global tests
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50590581
[30]Student accountability in post-Soviet countrie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59570_eng
[31]PISA results can lead policymakers astray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19/12/05/pisa-results-can-lead-policymakers-astray
[32]These are the German states with the best school marks
https://www.thelocal.de/20170425/these-are-the-german-states-with-the-best-school-marks
[33]https://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DEU&treshold=10&topic=PI

点击徽章,进入大象公会小程序▼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大象公会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