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位电影大师,我们可能真的欠他一张电影票
2019/4/7 0:01:00 秦朔朋友圈

·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589篇原创首发文章
娄烨,1965年生。
上海导演,水象星座(双鱼)。
关于如何描述我心中国内最好的两位(另一位是贾樟柯)作者型导演之一的娄烨,惯常的方法论或许会尽数失效,只因在“具体与抽象”“复刻与写意”“规律与灵感”“逻辑与偶然”的选项里,他的答案从来都是后者。

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公映之前,有着“中国伯格曼”之称的娄烨只拍了9部电影长片,其中7部主要通过盗版DVD传播,拿到龙标的2部里还有1部(内地公映版本)放弃了导演署名。

『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瑞典人,20世纪电影大师之一,代表作《野草莓》《芬妮与亚历山大》《第七封印》』
和同为国内第六代导演领军者的贾樟柯一样,娄烨也是拍独立电影出身,但与从《世界》(2005)时即转回“地上”的贾科长相较,后者“溯洄从之”的过程更显“道阻且长”的况味。
娄烨重回“地上”的标志是2012年公映的《浮城谜事》,又两年,他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拍出了《推拿》,在此之前,娄烨导演生涯更多的时间,都用于维护电影表达自由与艺术创作本身。在国内电影尚未建立分级制度之前,以娄烨为代表的更注重内容本身而非符号指涉的电影创作者,很难兼顾各方利害,达成面向未来的价值平衡。
故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之前,那句“我们都欠娄烨一张电影票”是最应景的言论,它不是矫情,而是实情。

影片海报上写的“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无声而有力,时间会是最好的明证,也会是唯一的明证。

女作家叶三在《娄烨:其实我别无选择》一文中记录过一件小事,它从侧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娄烨的角度——拍《紫蝴蝶》的时候,章子怡问制片人耐安:“姐,怎么导演从来不换衣服?”耐安回答:“导演每天都换,就是衣服都一样。”
一个人每天都换一样的衣服,说明他极度忠实于自我意识而非他人期待。别人觉得他是否有品、脏不脏、卫生习惯好不好,或是对其过往衍生出不良想象,统统不在考虑之列。
只做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忽略别人认为他不应当忽略的细枝末节,这就是内心强大者的一个特质。或许正是有赖于这份独特性与独立性,娄烨的作品才尤为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如果说韩国影坛最具“诗人”气质的人是李沧东,那么,这个角色在中国导演里,一定会是娄烨。

『李沧东(1954- ):韩国人,作家型导演,代表作《薄荷糖》《燃烧》《绿洲》』
在娄烨的电影中,“诗”与“歌”的意向或隐或显,始终缭绕。
它是《春风沉醉的夜晚》的结尾,郁达夫散文里的忧郁——“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也是《推拿》的开篇,海子在黑夜中的那首献诗——“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浮城谜事》城市立交桥两侧的落日余晖,杂中带序;也是《苏州河》中亘古绵长的船夫摇橹,泥沙俱在。
编剧梅峰甚至回忆,在《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剧本写作阶段,娄烨给他发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字画和《三言二拍》,力求一种“平面、断续、白描”的风格。
不仅画面极具辨识度,论起电影配乐的选择,娄烨的功力更堪称无人可望其项背。张惠妹、李志、尧十三、王杰等人的陈年旧作,均在娄烨幻世流年的光影之下声动梁尘,宛如再造。

娄烨的电影习惯肩扛跟拍、手提摇晃与运动构图,擅长描绘生活的混乱、游离与不确定,在这份独特的视听语言的背后,蕴含着创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私人发现。
那些难以名状的人性暗界,恰为普通个体无处安放的孤独、落寞、迷惘、伤感、悔恨提供了有力的注脚,娄烨的故事,从来是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你我的故事。他不爱拍“大写的人”,更偏爱边缘人与失语者,更注重他们的情绪落位与心结平复。娄烨故事朦胧、粘稠、晦暗的B面,潜藏着尾随而至、默不作声的人文关怀。
正似同样具备“诗人”属性的歌手朴树对《推拿》的观感,“没有狗血,没有卖弄聪明,没有照死里打,只有普通人寻常房间,妓女和瞎子的爱情,看不到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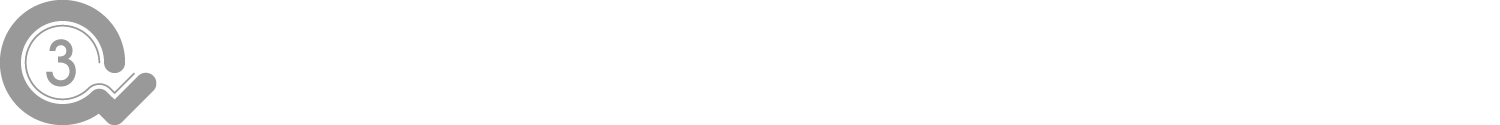
据说,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点映活动现场,饰演杨家栋警官的井柏然如是解析他对于片名的理解,“时代是风,欲望如雨,命运成云”。
去年的金马影展,娄烨接受采访时谈到过剧作建构的困难——“如果你去拍这段时间(改革开放)的纪录片,你会发现比剧情片还要剧情,因为它太戏剧性了,这就是实际的现实,就是像一个大起大落的剧情片一样。这个实际上对电影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真实的现实像戏剧一样,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在2003年之后,娄烨就已经计划要拍一部与改革开放有关的电影。创作者意识到,时代变革的大起大落,早已超过一部影片的承受范围,仅以美学方式或视觉方式去呈现那样一个多变的外部世界,无疑是一种不可能。因此,叙事角度和空间载体就变得至关重要,高楼林立之中作为旧年代遗留物的广州冼村,是娄烨寻觅到的对不同区间地域、不同发展速度的中国社会最有借鉴意义的压缩与杂糅。
当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故事背景虽与“冼村拆迁”有关,但它的内核仍可看做是一段畸恋,或是金钱与权力对在情欲中挣扎的普通人的异化。有人可能会说,那娄烨直接拍爱情不就完了吗,何必涉及官商勾结、权力腐败、强制拆迁等议题,何必花大功夫拍暴力场面?

我认为,这件事首先涉及不同人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其次,它是一个关于“尊重专业”的常识性问题。关于如何在作品中呈现自己对于时代变革与人的观察,娄烨一定比那类习惯在键盘上指导艺术家的观众更清楚。
况且,《战狼2》和《“大”人物》均有拆迁片段,未见差池,某些作为艺术创作表现对象的现实存在,实际远未到该令文艺工作者讳莫如深的程度。如果“热心观众”无法立足于客观实际,而是一味地自我设限,凭想象加戏,我们的文艺创作,无疑是前景堪忧的。

事实上,貌似叛逆的娄烨并非西方偏爱的中国导演类型,无论这个结论的范围是不是“第六代”。
娄烨是世界电影的公民,谁如果说他在镜头里“兜售苦难”,实属闭着眼睛说话,罔顾了《花》的编剧刘捷强调过的基本事实——“他一向站在平等的人的基础上来拍人,他的电影不是迎合传统西方对中国那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或异国情调的好奇,恰恰相反,娄烨的电影挑战并挫伤了某些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不得不平起平坐地看待他的才华和他的真诚。”
至于施展才华的时候沾染雷池,这不是艺术家的初衷,却也不应成为艺术家的回避。制片人耐安的觉悟是,“如果你打击了他,挫伤了他,他连热情都没有了,你还拍什么。”

我们的社会越发展,便越应当尽早明白:娄烨式的艺术家思考与投入的,永远是对人类真正有价值、有贡献的活动,它们就潜伏在那些看似疯狂、不可理喻的念头后面,这就像筛出金子的过程,沙石遍地,只为最后的一点闪光。
我很喜欢豆瓣网友puchinick的那句总结,它也正是我一直以来想表达的观点——“作为观众,即便是二流观众,你也有权利知道,你本来可以不用烂在啼笑皆非的电影院里,喂什么吃什么的,因为在同一片土壤之上仍有这样有勇气有创造力的作者。”
娄烨这样的创作者,不应只躺在迷影青年的硬盘里。

影视系列:
《燃烧》:毁灭的出路
《绿皮书》:美国精神赫然在列
《罗马》:世事万般波折,唯有相拥而眠
《地久天长》:时代巨轮与人性枪口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 图片 | 视觉中国 」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商务合作:biz@chinamoments.org
投稿、内容合作、招聘简历:friends@chinamoments.org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秦朔朋友圈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